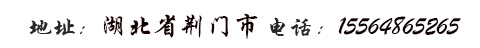一代狂徒的宏大理想
|
乌鲁木齐治疗白癜风医院 http://baidianfeng.39.net/a_bdfys/131211/4306092.html 几年前写了关于宏大理想两篇文章,写得悲情无比。今天主要内容就是大言不惭地讲故事,并且跟你们说一下老船长初心未改。 考古第一篇:宏大理想的捍卫者(年) 考古第二篇:宏大理想的恶敌与鏖战(年) 正文:一代狂徒的宏大理想 小时候妈妈告诉我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做人要温良恭俭让,谦卑很重要。朋友们也告诉我说你要继续这样骄狂下去有一天会吃亏。那个时候的国家领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长者,也告诉我们这代人要闷声发大财。我一句都没听进去。骄得忘乎所以,狂得小腚飘轻。十几年前仗着在辽南小城里的有名的小聪明,狂妄起来,真的是目中无人。互联网没有普及的时候在学校里怼老师怼校长怼教导主任,互联网普及之后则跨越山河大海怼天怼地怼空气。 十三年前我来北京求学后,这些年见到太多超乎想象的牛人。他们近乎魔幻地展现他们的智力、技能、谈吐和财富的优越性时,我觉得自己离有资格骄狂间还有一万个王思聪的差距。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年轻人应该都有这么一段年少轻狂的心路,它足够宝贵。而你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是或将要是我的学生,为师今天不跟大家讲历史学、政治哲学、西班牙语、英语、信息甄别力或批判性思维。今天我跟你们聊聊我对「年少轻狂」的理解,你们也可以知道孤阅这所理想中的大学是在怎样的一种心路历程中诞生的。 咱们就这样定个主题吧:骄狂可以,但必须有骄狂的资本。首先心态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骄狂资本。 这些年的纯个人经验告诉我,未富先狂,未强先妄这种蠢事最好少做。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讽刺民族主义者时如此英姿飒爽么?因为哥哥我曾经就是一名民族主义分子,还是行动力强的那种。你看这一届民族主义战狼根本就是战五渣,键盘鼠标皆为利刃,丝毫不懂得这里面的商机。而我十六岁那年就绕过校方阻拦组织了两场千人反日示威活动,焚烧日本国旗百余面。印刷的反日标语和小册子直接盘活了学校周边的快印店。而且在那些十几岁的小屁孩义愤填膺之时,我和我的朋友趁机兜售精心炮制的反日杂志,大卖两万元。钱拿在手里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已经不是民族主义者了。因为民族主义者的钱太好挣了,这么容易就被煽动起来进入癫狂状态,想必聪明不到哪里去。我那时天天自封天之骄子,如何与这些人为伍? 后来一个脱口秀演员一语道破天机:什么是民族主义——就是仇恨那些你从未遇见的人,并且骄傲于自己从未参与过的成就。然后我就悟了——不仅仅民族主义是这样,任何能够给人提供所谓归属感的主义和团体,都有可能是这样的。就像我是历史专业,我不去研究社会学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厌恶这个学科;而我的学术偶像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成就再高,也不是我的历史学成就。强行把自己行业顶级高手的荣耀标签贴在自己脸上,甚至不如碰瓷行为,因为起码人家碰瓷的大爷们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冲到马路上躺好凭本事吃饭。 于是乎,我就给自己定了个自我约束的规矩:要是不深入了解这寰宇万国,我就没理由跟着那些外交官僚义正言辞地喊打喊杀;要是未来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局交税交到手软,我就没脸说自己是个有主人翁意识的爱国者。 几乎每个二十岁一穷二白年轻男子都会在喝点小酒之后,吹牛说有朝一日要功成名就一统天下。大多数时候,王者的思想意识根本带不动青铜段位的行动能力。尤其是在北大这种牛鬼蛇神各路门萨俱乐部成员云集的地方,单靠做个乖乖学生对我来说想出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得出去看看。 所以行动力是第二个重要的骄狂资本。 至少对我来说,资源不在自己手里,知识不在自己脑子里,技能不在自己身上,我寝食难安。就算岁月静好生活安稳,我也会果断放弃迅速出逃去寻找机遇。 但那个时候,我根本没钱去英美发达国家体验生活。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于是我就想办法用各种野路子找到东欧的小国去谋个提供食宿且带薪实习的差事。现在我看有些孩子优柔寡断,凡事都求个确定性,不确定的事情不敢去尝试。在我这里这种观念就完全是荒谬的,你不尝试怎么能让不确定的事情确定下来呢?反正我那时候做什么事情机会成本都低得可怜,什么事情都愿意干。 二十岁那年我跟北大校方请了十五个月的假,说是最近心态崩了,去欧洲寻找下自我和方向,至少以后就业的时候不拉历史系后腿。校方相信了我的鬼话准了我这个长假。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在保加利亚的一所中学里,把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系统地跟一群中学生讲了一遍。本来是想去扬我国威,展示天朝上国的气焰与气质,做一个文化大使,结果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对吾国吾民的反思与批判。学期结束之后,校方赞赏我说一国之公民能如此深刻意识到本国的问题,中国前途无量啊。我当时愣住了,原来赢得尊重并不是靠气势而是靠真诚。说真的,现在每次有人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或者「给西方递刀子」这类话的时候我都能想到这段经历。 然后我又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在波兰的一个农场里当园丁除草抓虫,就是为了给当地主要是自闭症儿童的弱势群体创造一个美丽的生活环境。 人在东欧,就总想去西欧的花花世界看一看。其实穷不是周游列国的主要问题,野不野才是。于是我组装了个自行车用十四天时间从波兰出发,向南两千公里纵跨七个国家骑到梵蒂冈。我的塞班系统的手机充两个小时电能用十五分钟连个导航都没有,拿着破破烂烂的纸质地图抵达罗马城的时候,兜里只剩下二十欧元了。估计当年教宗列奥十世大发赎罪券的时候也没想到,几百年之后有个东土来的落魄青年会在圣彼得大教堂门口卖自行车换回波兰的盘缠吧。 这些事做了就是收益,不做就不知道收益是什么。十五个月的时间,首先就是学会一口杂牌国际英语和各种节省成本的生活技能。其次就是交朋友,直到现在,你提到东欧任何一个斯拉夫国家,我都能从通讯录里调出来至少十个能直接一个电话过去有求必应的铁子。另外更重要的是,形形色色的人见得太多,人这个概念就变得异常具象。我问我保加利亚的那帮中学学生问他们为啥都会这么多语言。他们就说,我没有你们这些大国人的包袱,我可不管哪个思想哪种理论哪个技能是哪国的,什么东西学到了就是我的,跟国别有什么关系——你看那天对你喊打喊杀的新纳粹光头党不也在努力学俄语和德语么。 而最大的收获就是,因为自己作为异乡人,要不断跟形形色色的人讲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这种终极问题,我发现了自己有做教育家的天赋。 但真正决定自己做教育还是要从燕园说起。 在北大,我们历史学系的人有个好习惯,就是一到周末就去海淀图书城扫旧书。当时买书八块钱一斤,我的一个拆二代师兄每周要开一个三轮车拉一百斤书回来,挑到好书自己看完再二十块一斤卖出去,妥妥的拆二代的地思维;我囊中羞涩,每周限制自己只泛读十斤。可就是这无产阶级的钱包支撑起了我资产阶级的梦想。 我当学生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遇见的老师们大多是无论多么学富五车德高望重,总归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为数不多的几位视角毒辣行事果敢的教授,一问渊源,不是文革时候吃过几年牢饭,就是上山下乡在黑龙江的农场里护理过产后母猪。想到自己总有一天告别北大去翱翔,但是一群没做过生意的人没遇见过大风大浪的老人家又如何教会我在江湖上闯荡维系我骄狂的本事呢?尤其是校园里的人依赖着国家财政拿着纳税人的钱对教育部慷慨扶贫,根本不可能利益攸关地去思考这个世界最敏感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做一名能够在历史中掀起一点波澜的教育家,就必须得有书斋之外的经验和理解。要不然,我说的话谁能信? 所以这第三个骄狂的资本,于我而言,是跨界视野。 于是我又有了新的狂野的想法,按大方向我要去一步步拿下做一个理想中的教育家的所有技能和资本。而我自由自在惯了,没办法按照官方的思路听别人智慧做什么。凡事按自己的意志做,就是有一个问题:成本和风险都要自己承担。挣一桶金能够起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挣过三桶金。每一桶都在撬动下一桶。 第一桶就是我在新东方靠体力活讲课挣了两年的工资。整个年,我工作三百六十三天,每天十二个小时起步。在办公室,老板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给我机会什么苦活我都愿意做,因为我想看看是怎样的基层运转逻辑能够支撑起一家纳斯达克企业;同时我又是北美英语考试的培训师,让我讲什么考试我都愿意。某一年夏天的暑期班一共61天,我讲了个小时的课,喝掉了两百杯咖啡。那两个月里听我讲课超过二十小时的学生有一万一千人。这是硬功夫,除了拿出最大的激情,容不得一点点偷懒。因为想要做个教育者,没有行业最顶级的教学经验,我拿什么去骄狂? 拿着两年攒下来的四十万元(按通货膨胀率,相当于现在的六十五万元左右)我定了一个目标,去一个拉美国家,从零干起,把四十万元全花掉,砸出第二桶金。而且这个行业不能是教育培训,必须变量分离——在教育资源被当局高度垄断的情况下,想要以在野的思路兴风作浪实现理想中的教育,就必须凭借商业的力量;而想做好商业化的教育,当个好老师是不够的,我必须同时是一个好销售、好市场、好商人。 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决定去撬动我的第二桶金——我想把中华茶道带到拉美,向一群习惯喝冰可乐冰咖啡和快餐的消费者坐在我的茶道馆里耐心喝一杯热滚滚的茶。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回去搞教育革命的胜算就又大了一分。 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跑遍了福建和云南的茶山与陶器厂,我读了所有唐宋茶道的典籍,我专门去中日友好中心跪得双腿失去知觉入门了日本茶道。我摸清了整条产业链的成本结构。我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一间破旧房屋改造成了茶道馆,没有汉式的家具就自己绘制找木匠打造,自己喷漆、手绘汉代瓦当装饰。然后打点海关和工商,把大批茶叶茶具弄进墨西哥。 其实还没有收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绝对是赚的——原因是没有这个疯狂的想法做依托,我不可能有动力去如此细致地研究研究某一个跨农业、制造业和零售批发的产业链以及两个国家的外贸细节。 茶道馆吸引的都是当地的富贵太太们,她们带着新鲜和好奇穿着汉服跪坐在茶道馆里,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跟她们介绍每一道工序与背后的中华文化,以及调侃邻居的寿司店老板是个假日本人,根本不懂大唐荣耀。 我从来没忘记做这件事的原始动机,最终还是要做教育。当时第一波在线教育浪潮兴起,于是我的生活就无比割裂:一大早起来在QQ群里免费讲英文版的西方文明简史,下午去茶道馆陪阔太太们喝茶打听墨西哥政商两界的花边新闻,晚上去梅里达中心广场跳萨尔萨广场舞陶冶情操。 四十万元花出去了的,生意收支相抵。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我获得了第二桶金,只不过它不是用货币来表达的,而是一些量化的收获,关乎于对人性最直观最核心的理解。我回忆了几个故事如下: 朋友来电话说是在危地马拉被当地村民绑架了。我拎着一兜子美元一脚油门跨境捞人的时候,才发现当地村民(所谓绑匪)各个都是穷苦的老实人,一边连连说对不起一边说你们先不要走,能不能帮他们演一演这出绑架戏,直到政府派人来跟他们谈判去表达他们对土地强制征收的反抗诉求。 我路过米却肯州一个沿途小镇的时候,在路口被一个持枪的小哥拦住,说镇子里他大哥在跟另外一个毒枭团伙枪战,怕伤及无辜群众,于是派他守一下镇口。等几个小时他们分出胜负清理尸体之后再进去吃饭。我跟他一起抽了根烟聊了很多,他给了念了两首美好的诗歌,表达了他对那个甩了他然后钻地道留在美国的前女友的思念之情。 我收拾行李从尤卡坦州离开去马萨诸塞州侨居之前,把所有的生活用品都留给照顾了我两年的女佣。我把物什送到她家的时候,才看到了她所在的街区的破落,与我的邻居们,那些制度革命党官僚们的女秘书们的深宅大院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见过香港的商人在跟墨国渔民捕捞太平洋海参的时候被假支票坑骗时华商与墨商剑拔弩张的对峙,我见过因为琥珀贸易在原住民和恰帕斯州当局爆发激烈冲突。他们语言不通,立场不同,无论是光鲜的西装革履,还是顶戴羽毛的传统打扮,都是一群为生计奔波甚至以命相搏的人在头破血流中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孤零零的定位,那种震撼无以言表。 而第三桶金的挖掘开始于这样一个事情: 我开车在尤卡坦州到金塔纳陆奥州的高速上,一个海洛因吸食过量的毒驾者失控直接将我撞出主路。我的脸砸向安全气囊的瞬间,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想法:妈的老子这满腹经纶和一身才华就这么香消玉殒了。从撞得稀巴烂还冒着滚滚浓烟的帕萨特爬出来,检查确定没有内出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白墨兮和黄河清通电话说,你们丫的赶紧辞职跟我创业——我们要为祖国之崛起而教书,挣大钱然后投资搞教育革命,培养几十万个眼睛里有光的年轻人带十四亿人翱翔——等教育部改革?家祭无忘告乃翁吧。 从此,每一天我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过。 于是就有了你们眼中的孤阅。 如果说我用以钞票表达的第一桶金,换来了用人性与共情表达的第二桶金,那么孤阅就是我用所有的沉淀、思考、行动、激情换来的第三桶金,这桶里装的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教育梦想,每一颗金子就是孤阅教育教育出来的时代英雄。 我前几天在孤阅以前所有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eidimalaa.com/wdmlms/6185.html
- 上一篇文章: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危地马拉总统先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